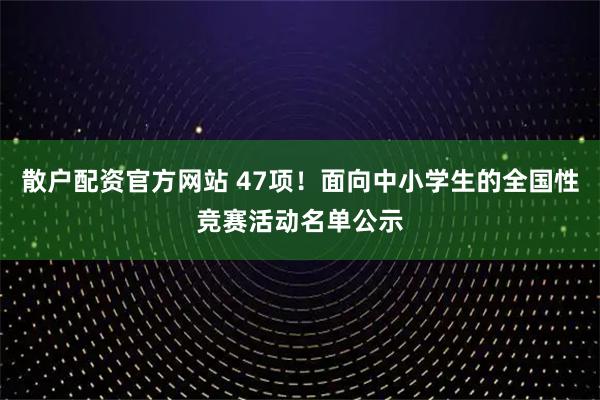"老头子散户配资官方网站,你炖什么呢?这么香!"奶奶端着碗,站在厨房门口。
"给娃炖鸡汤,下午就能喝。"爸爸头也不抬,只顾往锅里撒盐。
奶奶的脸立刻沉了下来,眉头紧锁,手里的搪瓷碗差点掉在地上。
我今年刚满五岁,爷爷去年冬天走后,我们一家三口搬来和奶奶同住四合院的老屋。
那是1985年的盛夏,院子里的老榆树叶子密得遮天蔽日,知了在树上不知疲倦地叫着"热死了热死了"。
单位分的筒子楼还没排到我爸名额,听说前面还有七八个等着分房的,我爸排到怎么也得等到年底。
四合院的西厢房就成了我们暂时的栖身之所,一进门是张红漆掉了大半的方桌,挨着墙放着两张木床,床头各有一个蓝布包袱,那是我和爸妈仅有的家当。
院里住着好几户人家,东厢是我三叔一家,他们在县医院工作,日子过得比我家宽裕些。
三叔的儿子比我小两岁,是个又瘦又小的男孩子,脸蛋白净,眼睛却总是无精打采,大家都叫他小豆子。
展开剩余94%奶奶最疼小豆子,常说:"老三一家忙工作,小豆子可怜见的,又瘦又小,得补补。"
院子里的老李婶每次见了小豆子都摇头:"这孩子,风一吹就倒啊,得多吃鸡蛋补补。"
奶奶因此变着花样给小豆子补身子,逢年过节,大街小巷都能见到奶奶拎着篮子,挑最新鲜的菜,最肥的肉,偶尔还能买到供销社刚到的糖果饼干。
我经常看见奶奶偷偷把家里唯一下蛋的老母鸡蛋留给小豆子吃,一边煮一边念叨:"得让小豆子长高长壮实,上学了可不能让人家笑话。"
那个夏天格外炎热,家家户户的木格门窗都敞开着,蚊香燃着,小蜻蜓围着蚊香直打转。
院子里一口水井,井台上放着半盆刚洗好的青菜,水珠顺着菜叶滴落,在水面激起一圈圈细小的波纹。
男人们光着膀子打着蒲扇,三五成群地聊着厂里的事,女人们围坐在老槐树下,谁家的缝纫机响个不停,谁又传出绗棉被的针线声。
中午收音机里的新闻联播刚结束,我从外面踢毽子回来,肚子饿得咕咕叫。
厨房里一个人也没有,锅台上的铁锅还冒着热气,灶台上搁着一个蓝边搪瓷碗,里面躺着一个刚煮熟的鸡蛋,散发着诱人的香气。
厨房墙上挂着的老式钟表滴答作响,已经十二点半了,我的肚子饿得直叫唤。
没多想,我就剥开壳,三两口把蛋吃了,还喝了口井台上的凉白开。
正擦着嘴,奶奶提着竹篮子进来了,篮子里是刚从生产队的地里薅回来的嫩豆角。
"谁让你吃的?"奶奶的脸一下子就变了,声音提高了八度,"那是给小豆子准备的!"
还没等我说话,奶奶放下篮子,抬起满是老茧的手,在我背上狠狠打了两下。
疼痛让我愣在原地,眼泪不受控制地流下来,滴在奶奶刚擦过的水泥地上。
"咱们家就那一只老母鸡,一天才下一个蛋,是留给小豆子补身子的!你这个馋嘴猢狲,连弟弟的东西都抢!"
奶奶的声音像院子里的大喇叭一样响亮,引来了邻居们的注意。
张婶探头朝这边看,王嫂停下了踩缝纫机的脚,李大爷从蒲扇后面投来探究的目光。
我的脸火辣辣的,既疼又羞,低着头不敢看任何人,只想找个地缝钻进去。
"孙子吃个鸡蛋怎么了?至于打孩子吗?"爸爸不知什么时候站在门口,衬衫被汗水浸透,脸上还有机油的痕迹,眉头紧锁地盯着奶奶。
奶奶气呼呼地说:"你儿子把小豆子的鸡蛋给吃了!那可是专门留给小豆子的!"
"娃儿肚子饿了,看见吃的就吃了,有什么了不起?又不是偷的外人家的!"爸爸拉过我,摸了摸我的脸。
"那是给小豆子补身子的!你儿子壮得很,不缺这一口!"奶奶忿忿不平。
爸爸看了看我,又看了看奶奶,沉默了一会儿,突然说:"那就把母鸡炖了喝汤吧,大家一起喝。"
这句话像一声惊雷,在狭小的厨房里炸开。
奶奶瞪大了眼睛,手里的扫帚啪嗒一声掉在地上:"你说啥?那可是下蛋的老母鸡!家里现在就靠它补贴日子!"
"一只母鸡有啥了不起,大不了我去供销社排队买一只,实在没有我去生产队借。"爸爸从兜里掏出皱巴巴的"大前门",磕出一根点上,深吸一口,烟雾在空气中盘旋,"我儿子吃一个鸡蛋还要挨打,那咱就把鸡炖了,以后谁也别惦记。"
三叔听说后,拖着塑料凉鞋从东厢房赶了过来,手里还端着半碗没吃完的挂面。
"老二,你这是干啥?不就一个鸡蛋吗?至于吗?家里就这一只下蛋的老母鸡,杀了多可惜啊!"
"就是一个鸡蛋,至于打孩子吗?"爸爸反问,眼神里带着少有的固执。
我躲在爸爸身后,看着大人们你一言我一语地争执着,眼泪顺着脸颊默默流下。
那时候我还小,不懂大人们为什么会因为一个鸡蛋吵得面红耳赤。
院子里的李大爷也来了,手里的旱烟袋敲着门框:"吵啥吵啥,一个鸡蛋至于吗?小孩子不懂事,大人嘴上说说就是了。"
奶奶气得浑身发抖:"你们懂什么!小豆子多瘦啊,开学就上学前班了,要是被同学笑话可怎么办?我这不是偏心,是实在心疼小豆子!"
争吵持续了半天,最后爸爸真的把那只下蛋的老母鸡给杀了,血滴在院子的石板上,很快被炙热的阳光晒干。
他熟练地拔了毛,掏了内脏,切成块,放进家里最大的铁锅里,加了姜片和葱结,小火慢炖。
铁锅里很快飘出浓郁的香味,引得院子里的小孩子们都围了过来,咽着口水。
爸爸特意盛了一大碗给我,里面有一只完整的鸡腿,那在当时可是顶顶珍贵的东西。
"儿子,记住今天,"爸爸蹲下身,平视着我的眼睛,"这世上没有什么不能商量的事,但有些东西,不值得为它伤了感情,可也不能因为怕伤感情就委屈了自己。"
那是我第一次喝到如此鲜美的鸡汤,香浓醇厚,可心里却怎么也高兴不起来,总觉得那汤里有说不出的苦涩。
那顿饭后,奶奶气得好几天没和爸爸说话,饭菜都是妈妈做好送到她屋里。
院子里的氛围也变得微妙起来,三叔一家见了我们,总是绕道而行。
晾衣服的时候,三婶还会特意等我妈收完衣服才去晾晒,仿佛碰到了我们家的东西会倒霉似的。
我因为这事成了院子里的"坏孩子",王婶家的大头和李婶家的小花都不愿意和我一起玩滚铁环了。
"他偷吃别人的东西,大人还护着他,太不要脸了。"一天,我在井边打水,听见王婶子对着李婶说。
"可不是嘛,还把下蛋的老母鸡给杀了,这不是跟自家过不去嘛!"李婶接茬道。
这些话语像无数小刀子一样扎在我幼小的心灵上,我开始变得沉默寡言,放学后就躲在家里不出门,害怕面对邻居们异样的眼光。
有一次,小豆子在院子里玩时,不小心把球踢到了我家窗户上,我刚想把球扔回去,三婶就厉声喊道:"别碰我们家的东西!谁知道你手干不干净!"
我僵在原地,手里的球掉在地上,滚到了角落。
回到屋里,我偷偷躲在被窝里哭了一场。
那天晚上,我听见爸爸和妈妈在柴火房里小声交谈,老式马灯投下摇曳的影子,让他们的脸忽明忽暗。
"你当时何必那么冲动呢?一只下蛋的母鸡多金贵啊,粮站的票都不好开,肉票更是难得。"妈妈叹气道,手里的针线活停了下来。
"那你想让儿子因为一个鸡蛋被人瞧不起一辈子?"爸爸的声音很坚定,"鸡蛋没了可以再买,母鸡没了可以再养,但孩子的自尊心伤了,可就难修复了。"
"可是现在全院子的人都说咱们不讲理,小宝连院子都不敢出了..."
"人言可畏,可也不过是一时的。做人要有骨气,不能因为怕别人说闲话就委屈了自己的孩子。"爸爸用力拍了拍马扎,声音低沉而坚定,"再说了,家里人偏心,外人偏向,难道咱就眼睁睁看着儿子受气?这要是从小就忍,以后遇到天大的委屈,不也得忍着?"
爸爸的话让我在黑夜里偷偷抹眼泪。
我第一次感受到,原来父爱也可以这样刚强而温暖,如同炎炎夏日里的一杯井水,不声不响,却在最渴的时候给了我最大的慰藉。
炎夏过去,秋天的风带走了最后一丝暑气,枯黄的叶子铺满了院子,发出沙沙的声响。
一天,我放学回家,看见院子里停着一辆带斗的旧拖拉机,爸爸和几个工友正往上搬家什。
"咱们家终于分到了单位的新房。"妈妈兴奋地对我说,眼睛里闪着光,"以后有自己的房子了,还有独立的厨房和卫生间呢!"
搬家那天,院子里的不少人都来帮忙,李大爷、张婶子甚至连平日不怎么说话的刘师傅都来了,唯独三叔一家和奶奶站在一旁冷眼旁观。
临走时,我鼓起勇气去和奶奶道别,却被她扭过头去避开了。
她站在老槐树下,背影有些佝偻,秋风吹乱了她的花白头发。
"妈,我们走了。"爸爸放下手里的蓝布包袱,低声说道,声音里有说不出的复杂。
奶奶没有回头,只是背影微微颤抖,手紧紧攥着围裙的一角。
就在这时,小豆子从屋里跑出来,手里捧着一个用红纸包着的煮鸡蛋,塞到我手里:"表哥,这是给你的,我让三婶给我煮的。"
这个简单的举动,让院子里一时安静下来,连秋风卷起落叶的声音都清晰可闻。
我接过鸡蛋,感受着透过红纸传来的余温,眼泪在眼眶里打转。
"谁让你给他的?拿回来!"三婶从厨房里冲出来,脸色铁青。
小豆子撅着嘴说:"我就想给表哥吃。上次他吃了我的鸡蛋,害得大家都不高兴,我不想大家不高兴。"
"这孩子..."三婶语塞,尴尬地看着四周的邻居。
孩子纯真的话语像一道亮光,照进大人复杂的世界。
三叔的表情变得尴尬,抽了抽嘴角,喃喃道:"小孩子不懂事..."
奶奶转过身来,眼中闪烁着复杂的光芒,嘴唇动了动,却没说出话来。
"好孩子。"爸爸摸了摸小豆子的头,然后看向奶奶,"妈,我们走了,您保重身体。有空我们会来看您的。"
奶奶终于开口:"你们...有空常回来吧。"虽然语气还是生硬,但已经是一个缓和的信号。
我们坐上拖拉机,驶出四合院的大门,小豆子一直追着跑了一段,直到拐弯处才停下来,挥着小手。
新家在县城东边的筒子楼里,两室一厅,虽然不大,但终于有了独立的空间。
我和爸妈睡里屋,外屋是客厅兼餐厅,小阳台上还能种几盆花草。
搬到新家后,我们的生活发生了很大变化。
不用再担心上厕所撞见邻居尴尬的目光,不用为了洗衣做饭排队使用公共空间,再也不用为了一点小事和邻居磨面皮。
爸爸的工资也涨了,从四十五元涨到了六十二元,家里条件渐渐好起来。
每个周末,妈妈都会做些卤肉、蒸饺子之类的好吃的,爸爸就骑着凤凰牌自行车,带着我回老院子看奶奶。
一开始,奶奶总是板着脸接受我们带去的东西,话也不多,只是简单问问生活怎么样,工作顺不顺利。
后来慢慢地,她会留我们吃顿饭再走,饭菜也越来越丰盛,从最初的白菜豆腐汤变成了红烧肉、糖醋鱼。
有一次,奶奶特意熬了鸡汤,盛了满满一碗给我,里面还有一整只鸡腿,那正是我当年最爱吃的。
三年后的一个夏末,天气已经转凉,爸爸突然说要带我回老院子看看。
"你奶奶病了,"爸爸解释道,拿出一个油纸包,里面是刚从药房买的药,"三叔来厂里说,她总念叨你。"
回到熟悉的四合院,物是人非。
老榆树依旧,叶子已经有些发黄,几个歪脖老槐还是那么挺拔,井台上的青苔更厚了,但院子里的人少了许多。
听说李大爷一家搬到了儿子的新房子里,张婶去了南方跟女儿一起做生意,王嫂家也分到了新房。
奶奶躺在东厢房的炕上,被子叠得整整齐齐,炕桌上放着一杯热气腾腾的枸杞水,墙上挂着一张我们全家的老照片,那是爷爷在世时照的。
奶奶看起来比三年前苍老了许多,脸颊凹陷,头发全白了,眼眶深陷。
见到我们,她的眼睛亮了起来,挣扎着要坐起来。
"别动,别动,"爸爸赶紧扶住她,"躺着就行。"
"长这么高了..."奶奶虚弱地说,伸手想摸我的头,却因为无力而半途落下。
我赶紧握住奶奶的手,那手粗糙干瘦,布满老茧和皱纹:"奶奶,我想您了。"
奶奶的眼眶红了,眼角渗出泪水:"奶奶...对不起你..."她的声音几乎微不可闻,"那天不该为了一个鸡蛋打你。"
我摇摇头,眼睛也湿润了:"奶奶,是我不好,不该偷吃小豆子的鸡蛋。"
"傻孩子,"奶奶艰难地笑了笑,"一家人哪有什么偷不偷的?奶奶是心疼小豆子,却忘了你也是奶奶的亲孙子啊。"
爸爸站在一旁,默默地抽着烟,眼圈微红,烟灰掉在地上,他也没顾上弹。
窗外传来一阵嬉闹声,小豆子从外面跑进来,他已经长高了不少,变得结实了,脸上有着健康的红晕。
看见我,他咧嘴一笑,露出刚换的大门牙:"表哥!你们来啦!"
那天中午,三叔杀了只鸡,炖了一锅香喷喷的鸡汤。
全家人围坐在一起,氛围融洽,连平日里话不多的三婶也变得健谈起来,说起了小豆子上学的趣事。
奶奶特意给我盛了一大碗鸡汤,还夹了几块鸡肉放在我碗里。
"多吃点,长高点。"奶奶慈爱地说,眼神柔和得像化了的黄油。
那一刻,我忽然明白了,爸爸当年为什么要把那只母鸡炖了。
不是为了一时意气,不是为了和奶奶对着干,而是为了打破那个看似不可触碰的规则,捍卫一个孩子的尊严。
在成人世界的矛盾和偏见面前,他用自己的方式告诉我:人活着,要有骨气,不能因为别人的目光就委屈了自己。
吃完饭,我和小豆子在院子里玩耍,秋日的阳光透过榆树叶的缝隙,在地上投下斑驳的光影。
我们蹲在地上玩着打弹珠的游戏,小豆子的手法娴熟,几下就把我的弹珠全部打了出去。
"表哥,我妈说你爸当年太任性了,为了一个鸡蛋杀了下蛋的母鸡。"小豆子忽然说,拨弄着地上的小石子。
我笑了笑:"那不是为了一个鸡蛋,是为了一个道理。"
"什么道理?"小豆子好奇地问。
"就是..."我思考了一下,"就是每个人都值得被公平对待,哪怕他只有五岁。"
小豆子似懂非懂地点点头,又低头玩起了弹珠。
我抬头看向老屋的窗户,奶奶和爸爸正坐在一起,说着什么,奶奶的脸上有着久违的笑容。
那年冬天,奶奶的病好了,她决定和三叔一家一起搬到县城里居住。
她说:"一个人住在老屋里冷清,还不如热热闹闹的好。"
多年以后,我成家立业,有了自己的孩子。
每当回忆起那个因一只鸡蛋而起的风波,我都会感慨万分。
那只被炖成汤的母鸡,那碗承载了太多情感的鸡汤,教会了我生活中最宝贵的一课:亲情不该有偏颇,尊严不容被践踏。
如今,我常带着孩子回老家看奶奶。
她已经八十多岁了,身体硬朗,背有些驼,但眼神依然明亮,爱笑爱闹,总说自己还能再活二十年。
我们一家人围坐在新房的大圆桌旁,吃着热气腾腾的饭菜,奶奶依然喜欢给我们煮鸡蛋吃。
每次煮好后,她总会微笑着说:"这回够吃了,一人一个,谁也不许抢。"
然后又偷偷多给我的孩子夹一块肉:"乖孙子,多吃点,长高点。"
而我和爸爸则会相视一笑,因为我们都记得那个夏天的教训:有些时候,一碗鸡汤的意义,远远超过了一只母鸡的价值。
当年五岁的我不会想到,这件小事会成为我一生的财富。
它教会我如何坚守原则,如何在不公面前保持尊严,如何在委屈时不轻易低头,也让我明白了家人之间的宽容与理解,才是维系亲情的根本。
每每想起,那碗鸡汤的香味仿佛还萦绕在鼻尖,温暖而深长,就像爸爸的教诲一样,历久弥新。
"小时候的一碗鸡汤,暖了一生。"这是我常对孩子说的话。
而他总是好奇地问:"爸爸,那鸡汤真的有那么好喝吗?"
我笑着揉揉他的头:"不是汤好喝散户配资官方网站,是那碗汤里有爱和尊严的味道。"
发布于:河南省金华配资提示:文章来自网络,不代表本站观点。